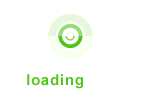20世纪90年代,我读职业高中,学啤酒酿造专业。这专业冷门,据说当时全国仅两个学校开此专业。按理说物以稀为贵,此专业的毕业生应该抢手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啤酒厂倒是很欢迎我们去做临时工,而且是仅需要能干重活的临时工。至于技术人才,厂里早已满员,再说他们也不需要过多的技术与研发。
我最初的工作是扛包,就是将仓库里的大米包和大麦包扛上车,然后运至车间。大米包180斤,大麦包160斤,我一天要扛二百多包。虽然我刚20岁,来自农村,之前也干过不少农活,但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,我还是吃不消。母亲给我织的那件红毛衣,整个白天都被汗水泡着,于是里面的白衬衣都被浸染,成了红衬衣。每当夜里醒来时,浑身的每个关节都是痛的,包括手指关节。这些还是小事,真正让我痛苦和迷茫的是,我根本看不到希望和出路。啤酒厂座落在山清水秀的大山脚下,甚至比我的农村老家更偏僻落后。厂里的工人大多是附近的农民,他们上班务工、下班务农,有粮有油有工资,便觉比其他村人高出一筹了。
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
后来我被调去后酵车间,三班倒,劳动强度也小了很多。夜里没事时,工友们会凑到门口谈天说地。他们说美国的首都是意大利,说老鼠吃盐会变成蝙蝠,说最新研制的炮弹能绕地球飞两圈,说能存下3万块钱的话这一辈子就不用干活了……我突然很怕变成他们,怕这种甘于愚昧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。
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我把辞职的决定告诉了一同进厂的几个同学,他们很是震惊。一个女生说,你可千万考虑好,咱农民的孩子找份工作不容易,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当时我就想,也许她可以一辈子窝在那里,但我做不到。
我就这样离开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工厂。学了3年啤酒酿造专业的我,从那以后再没有从事过与啤酒酿造相关或沾边的职业。
回老家待了一个多月后,一个同学将电话打到村里,说她打工的那家厂正在招工。那个生产钓鱼竿的工厂很大,在城市里。虽然钓鱼竿不是我的追求,但它有着农村孩子所向往的灯红酒绿。我想,这也是那个年代很多农村孩子跑到城市打工的原因——尽管那些灯红酒绿其实与他们并无关系。
在那个厂里,我负责的工序是“面漆”,即给上过底漆的鱼竿再上两遍“表面的漆”。这工作不难,但长期与油漆打交道,对身体危害极大。工厂有一万多人,仅我所在的面漆车间就有三百多人,而这样的车间,厂里有十几个。宿舍里住着四十多个人,不同的生活习惯与作息时间,使得里面时刻有人在睡觉、吃东西、喝酒、打牌、聊天,到处都是扯起的绳子、湿漉漉的衣服、方便面包装袋、臭哄哄的鞋子和没洗的袜子……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脚臭与发霉的气味。只有在工厂定期检查卫生的时候,宿舍里才会相对干净一些。
厂里有3个食堂,逢吃饭时,每个食堂都乱哄哄的像农村大集。吃饭的饭票是拿粮去食堂换,菜票则要用钱买。那时大家工资很低,所以到了月底,很多人往往只剩下饭票而没有菜票了。还记得一次因为临近过年,食堂举行大会餐,就是说让工人们白吃一顿。刚好宿舍里有个男孩已弹尽粮竭,就在会餐前饿了整整3天——白天照常上班,到饭点就躺回宿舍。那次会餐,四两一个的馒头他吃下6个,几口就吃完了。
工厂唯一的娱乐设施是一个舞厅,里面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套音响设备。但更多人把它当成一个社交场所,既不看电视,也不跳舞。我去过一次,恰好看到了一则广告,说某公司招聘服装设计。在那个嘈杂并混乱的环境中,我努力记下地址与电话,第二天去考试,竟然被录取了。而之前,我从没有系统地学过美术,对服装设计更是一窍不通,所以我一直坚定地认为,艺术这件事真的是天生的。
在做过一段时间的服装设计之后,公司倒闭,我又重回打工生涯,陆续干过锡镶厂、铝合金厂和皮鞋厂,这些工厂大同小异,基本都是工作累,工资低。工友们发了工资大吃大喝,没钱了就硬挺着。休息的时候,大家要么打牌,要么喝酒,要么睡觉,要么到处乱逛,要么重复“老鼠吃盐后就会变成蝙蝠”这类“常识”……在一个甘于平庸的环境里很难有斗志,甚至很难保持清醒。那个年代,几乎天天都在混日子的人,也并未撑起自己的生活。
好在我并未完全放弃自己。那些年我读了很多书,文学、哲学、数学、历史……后来,我彻底离开那样的工厂,日子虽清贫了些,却是我想要的生活状态。
直到现在,我也始终相信这样的道理:假如没人给你搭建一个舞台,那么,除了自己搭建,别无他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