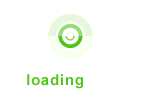有一年年底,一家刊物与青啤集团联合搞了个征文活动,主题是“我的青啤记忆”。看了征文启事,勾起了我关于青啤的一些温馨记忆。于是,便草就一篇小文应征。由于征文字数限制在一千字之内,故而小文虽被采用,但仍有些意犹未尽之感,觉得还有些该说的话,很有必要再说上一说。
一
我虽非善饮一族,但喝点小酒的事情还是时常发生的。或许是“两害(难受)相较取其轻”的缘故,在所有酒类中,我比较偏爱啤酒。在各色啤酒中,我又特别钟爱青岛啤酒。
我与青啤结缘,源自于我的一次未能尽兴、但却充满温情的小饮之经历。1976年冬,我结束了插队,被招工到了莱州湾畔的一家小造船厂。与我处得不错的两个青岛知青,很热心地请了假陪我去厂里报到。到了工厂驻地,我才知道那儿是那么偏、那么小,心中不免就有了一种茫然与凄凉之感。两个同伴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就劝我说,招了工总归是件好事,值得庆贺一下。报上到之后,他俩非要请我吃饭,硬把我拉到了镇上唯一一家国营小饭馆。点酒的时候,那俩伙计惊喜地发现,这小店里竟有青岛啤酒。记得是那种棕色小瓶装的,大约三毛来钱一瓶。高兴之余,他俩便决定这餐饭喝啤酒。
我在济南读中学的时候,夏天经常看到一些大人光着膀子蹲在马路边,端着粗瓷大碗,有滋有味地喝那种两毛钱一碗、颜色棕黄的散啤酒,就很有些好奇。无奈家中管制甚严,更兼囊中羞涩,一直未能有机会品尝一下那玩意儿,看看究竟是个啥滋味儿。中学一毕业,我就下乡插队去了。下乡之后,只是偶尔跟乡亲们凑凑热闹喝几口白酒而已。乡亲们对啤酒不感冒,少数尝过的人一致认为那东西有股马尿味儿。
对这东西不甚了解,再加上价格原因,我就不太赞成喝啤酒。那个时候,一瓶白干酒也就六七毛钱,两小瓶啤酒的价钱就赶上一瓶白酒,而我们仨一瓶白酒足够了。听他俩说,啤酒的度数很低,喝起来跟水差不多,青岛就有人把啤酒称为“啤水”,那我们仨得喝多少瓶才够呵!
架不住他俩一力撺掇,再说是人家好心掏钱请客,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。当酒液缓缓倒进玻璃杯子之后,金黄纯净的酒体、洁白细腻的泡沫,在灯光的映照下,闪耀着温润的光泽,一下子给了我一种舒适温暖的感觉,尽管此时正值隆冬。第一杯酒喝下去,一股混合着些许爽利苦味的清香,从丹田冉冉涌起,口中也隐隐有种麻酥酥的针刺感。他俩定定地望着我,期待地问我感觉如何,我说还行。他们就很高兴,对我说了很多关于青啤的事情。比如德国的生产工艺、澳大利亚的啤酒花、加拿大的大麦、崂山的矿泉水什么的。也许就从那一刻起,我开始被青啤所吸引。
推杯换盏之间,他俩一个劲儿地劝慰我不要灰心,说只要好好干,将来有参军提干、上大学之类的机会,还是可以回到大城市的,并真诚地欢迎我今后能去青岛工作。于是,我们便频频地为将来能够在青岛重逢、畅饮青啤的美好期望而干杯,我的心情也慢慢地好了起来。承蒙他俩吉言,1978年我还真就考上了大学,毕业没多久,又调到了省直机关工作。
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的,没多会儿十瓶酒便落了肚。兴致正盛、酒意微酣的我们再去要酒的时候,服务员却说,青啤是紧缺商品,上面定量分配,店里就来了十瓶,都被我们给喝光了。幸亏当地人不认啤酒,否则早就卖完了。我们便问是否还有其它牌子的啤酒。服务员答道,没听说过别的牌子的啤酒。也难怪,雨后春笋般到处都有啤酒厂,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了。
二
有些人认为青啤比较杀口、劲儿大,因而不太喜欢青啤。殊不知,这正是正宗青啤的独到之处。在这一点上,我很赞同省内一位著名教授关于青啤的看法。
青啤紧缺商品的地位,在我印象中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。在这之前,市面上极少供应青啤。即使是青岛市民,也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,每人或者每户才能凭票证供应几瓶。因而,那时青啤属于难得一见的金贵东西。
1986年夏,我们单位在青岛组织了一个学术研讨会,我在会上服务。会议邀请了一些著名教授学者参加,其中有位省内某名校的教授,经常参加我们单位组织的活动,故而与我相熟。有天晚餐时,他老先生神神秘秘地对我说:“小王,晚上忙完了一定到我房间来一趟啊。”我问他有啥事,他秘而不宣:“来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等我忙完了会务上的事情,赶到他房间时,已经九点多了。他没锁门,可能是在等我。我推门而进之后,看到老先生翘着个二郎腿儿半躺在床上,一手攥着个啤酒瓶子,一手拿了本书在看。见我进来,老先生忙不迭地下床,一脸歉意地对我说:“你看看,你看看,真不好意思!我看你整天忙前忙后地挺辛苦,本想请你好好喝一气正宗青啤犒劳犒劳你。都怨我没出息,这一会儿你没来,就让我给喝得只剩下一瓶了!”
原来,老先生有个学生在青岛啤酒厂工作。听说老师来了,便给他送来了一盒出口青啤,十二小瓶装的。老先生觉得挺珍贵,就邀我一同分享。这老先生平时就比较喜欢喝啤酒,便一边以酒当茶,一边看书等我。一来二去的,两个来小时的光景,那一盒啤酒就快被他给整光了。在我喝着剩下的那一瓶啤酒的时候,老先生对我说,只有青啤这种略带苦头儿的杀口劲儿,才是真正的啤酒味儿。其他牌子的啤酒喝下去酸不溜叽的,严格讲来就称不上是啤酒。可青啤也太稀罕了,在青岛开会也喝不到正宗青啤。见到学生送来,自然有些喜不自禁,喝起来也就把持不住了。
除此之外,还有一件与青啤有关的事情也挺有意思。那年,我随团去西欧培训。在奥地利维也纳的时候,有天晚间,一位同伴非要拉我去体验一下小酒馆的感觉。他的英语水平马马虎虎,不像我只会蹦单词儿。有他相伴,我们出去语言方面可以对付一气。
我们来到驻地附近的一家小酒馆,里边没有客人,只有一位胖胖大大的老板娘,百无聊赖地趴在柜台上发呆。我们用比较生硬的英语对老板娘说,我们要喝“比尔(啤酒)”。老板娘见来了客人,立马来了精神,很热情地操着同样生硬的英语,给我们推荐了几种“比尔”,比如慕尼黑的、法兰克福的、维也纳的,等等。我们说,就喝“维也纳比尔”吧,在维也纳,喝“维也纳比尔”才有味儿嘛!“谁不说俺家乡好”,我们的话把老板娘忽悠得有些找不着北,她咧开嘴巴爽朗地放声大笑起来。高兴之下,一人又额外送了我们一瓶“维也纳比尔”,并说她知道中国有“青岛比尔”,“青岛比尔”也“歪儿瑞(很好)”。听了老板娘的话,我们同样兴奋莫名,便邀她一起为“维也纳比尔”和“青岛比尔”干杯,把她高兴得又是一通大笑。
三
如今,青啤作为紧缺商品的日子已经成为记忆,假若把贴着青啤牌子的啤酒都看作是青啤的话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,青啤集团开始巨镰割草般、或者说是风卷残云般收购兼并各地的啤酒厂。山东境内大大小小的啤酒厂,有一多半齐呼啦地改换门庭,投靠了“威虎山”,遍地是青啤的局面随之出现。
美中不足的是,这些被兼并啤酒厂的产品,尽管贴上了青啤的牌子,甚至也按青啤的工艺流程进行生产,但它们在原料、水质等方面的先天不足,短时间内还是难以弥补的。因而,此青啤之味道非彼青啤的事情,还是经常发生的。青啤,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紧缺。
有个我很熟悉的小啤酒厂,在兼并大潮中摇身一变,也成了青啤集团的众多子孙之一。这个厂原先出产的XX牌啤酒,尽管广告做得天花乱坠,但当地消费者却并不买账,谑称其为“一瓶倒”。意思是喝这种啤酒不用多,一瓶准醉。关于这个雅号,在当地还有个流传较广的笑话。说是警察抓住了小偷,在审问的时候,都会问他是愿喝啤酒还是挨电棍。小偷便说,那当然是喝啤酒了。于是,警察就拿出了那种号称“一瓶倒”的啤酒。小偷见状,连忙改口说,那你还是干脆给我一电棍得了。再次声明,此为笑谈,当不得真,更没有影射指责警方刑讯逼供犯人的意思。
青啤留给了我很多温情脉脉的记忆,因此我很怀念原汁原味的青啤。我也很希望那些被青啤兼并的品牌,不要贴上青啤的商标就万事大吉。纵使难以做到跟正宗青啤分毫不差,起码也得八九不离十。在这方面,青啤的责任更大。人们喜欢怀旧,是由于过往有些美好的东西值得怀念。人们如果对从前的某种产品、某种品牌念念不忘的话,只能证明如今它们的同类已乏善可陈。兼并不只是占有市场的一种手段,它更应该是品牌文化的光大与延展。譬如说,“一瓶倒”通过兼并脱胎换骨,那儿的百姓可以自豪地说“让‘一瓶倒’见鬼去吧,俺们家乡也出正宗的青啤了”,那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。倘若只是新瓶装旧酒,即使贴的牌子再花哨,也是白费心思,于事无补。
有些遗憾的是,来到省城工作之后,去青岛出差的机会多了以后,我曾多次打听过那俩鼓励过我、使我爱上青啤的伙计之下落,期待着与他俩痛饮青啤,畅话旧谊,以弥补那一次未能过瘾之遗憾,但却一直未能如愿。
近些年来,单位每年都组织查体,我的某些指标偏高,医生力劝我戒酒,特别是要告别啤酒和白酒。白酒无所谓,我原就基本不沾这东西。但对啤酒尤其是青啤,我还真是有些难说再见。请注意,我说的是真正的青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