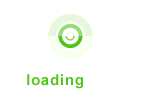好汉不提当年勇,济南啤酒也曾称雄天下。我在济南的那些年,泉城的爷们谁喝青岛啤酒啊!白酒品质看粮食,啤酒好喝看水质。趵突泉水甲天下,自然酿得出天下最好的啤酒。
1984年,单位分来十几个大学生,周末娱乐就是轮流请客喝啤酒。大家骑自行车从南山飞驰而下,顺河街找家有厕所的小酒馆,一盘花生毛豆,一盘嗄拉油子,一盘海米拍黄瓜,刚发工资时会要份辣炒花蛤,加盘酱猪蹄。那时的啤酒还装在大衣橱一样的巨大冰柜里,要一扎一扎的压出来。年轻人豪爽,大玻璃杯一扎,一饮而尽,谁也不偷奸耍滑。一直喝到小饭店打烊,我们便骑上自行车,东摇西晃、鬼哭狼嚎地穿过夜晚空荡的大街。酒精与荷尔蒙共舞,啸叫与歌哭齐飞,人不放荡枉少年。
一起喝酒的朋友中,小郭瘦得像麻杆儿,每次都是他张罗,也最能吹牛。小宋体壮如牛,每次都是他跟小郭互怼,小郭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小年是个安徽人,更在乎酒后晕乎乎的状态。小邵平时话不多,喝酒一杯脸就红。小钟很有艺术气质,酒后双手如乐队指挥一样舞于空中,独自陶醉,旁若无人。小刘人长得白净帅气,酒风犀利,大学毕业时女朋友分到外地,但他的钱包里总是装着那个笑靥如花的女孩的照片,照片背后写着“给我的太阳神”,两人鱼雁往还,很是让我们这些单身汉羡慕。
后来同事中一位厅长的女儿看上小刘,小刘左右摇摆难于抉择,终于架不住厅长千金的进攻。小刘说动我们赴他新女友的家宴,厅长很客气地敬了一杯茅台便退了。那顿饭,海参大虾应有尽有,算得上奢华,但大家吃得很沉闷,觉得小刘喜新厌旧攀龙附凤,后来便疏远了他,出去喝酒也不再叫他。今天想来,人家个人的选择,与我们有个毛线关系?可那时觉得,做人是要有原则的。
那时济南的啤酒名气很大。白马山啤酒厂的白雪清爽、北冰洋浓郁,在全国的声名绝对压过青岛啤酒。济南啤酒品牌,听名字就觉得冰爽诱人,夏天就自然喝几杯次。一次去青年干部学院的宿舍,四个大学同学在二楼喝酒,找个学生用大铝壶到一楼的饭店里打啤酒,回来倒在一个大脸盆里,那个学生竟然供不上我们喝。
济南啤酒厂后来出了黑帖趵突泉,俗称黑趵,味道醇厚,后来居上,一时风头无两。如果没有点关系,根本提不到货。一次,我们和一位记者以采访的名义到济南啤酒厂,拜见到那位留着平头又黑又瘦象个村支书一样的厂长,他也就批我们十箱,那已是很大的面子了。后来瓶啤日渐风行,酒店都会有个大盆,泉水浸泡着瓶啤,温度刚好。不似今天冰箱里的拿出的啤酒,榨牙。
济南的啤酒好喝,平时喝得开心,并不留意自己的酒量。某日我姑父请了两个朋友在家喝酒。姑夫老家菏泽,桌下一捆菏泽产的冰源啤酒,姑夫说我瘦弱,让我喝啤酒,他们喝白酒。一位客人说自己家有黑趵,大家便窜掇他开吉普去拉来一箱,打开一瓶三人各尝一杯,然后继续喝白酒。我兀自一杯杯喝啤酒,听他们聊天,不时用大杯啤酒敬他们小杯白酒。酒局从中午喝到傍晚,我把所有的啤酒都喝光了,那是我自己非常清醒的记录,一顿喝了三十三瓶。一向以酒量大著称的姑父,此后从不跟我拼酒。
那时对吃食不太讲究,有几个凉菜下酒便是。济南还没兴起撸串喝酒的习惯,槐荫区一带有过烧烤,但路途太远,没有去过。倒是后来在经十路和青年西路交叉口的云亭火锅火了好一阵子。大夏天一边用铁纤子捅火锅,一边喝冰啤酒,很过瘾。省府前街上有一家做酱油螺蛳的小店,一间门头总是挤满了人。店主是个胖胖的大嫂,脖子上晃动着金链子,手上几只硕大无朋的金戒指,嘴里叼根烟,一手拎酒端菜,一手抓把票子收款。
你叫声“嫂子,有地儿吗?”她总能在已挤满人的桌子再挤下几个人。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全济南螺蛳都叫嘎拉油子,只有这一家叫酱油螺蛳。她家的螺蛳的尾部用钳子夹掉,加上葱姜辣椒大火烹炒,非常入味,且很容易吸出壳中螺肉。告辞时,大嫂用她抓一把钱的胖手砸一下客人肩膀,从嘴角挤出一句“兄弟再来”,扭头又招呼新来的客人。
那些年山东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啤酒,各地的啤酒在济南都能见到,琥珀、沂蒙、三孔偶尔也尝一瓶,对济啤却痴心不改,极为磁诚。后来朝山街上有了酒店自酿的啤酒,紫铜的发酵罐摆在店堂里,很是气派。自酿啤酒虽然新鲜,却容易上头,也喝得不多。
世纪之交,我离开了生活了16年的济南。行前一月,开始一场接一场告别酒,场场大醉而归,终至胃病发作。每天抱着肚子在床上滚来滚去,缠绵悱恻而又汹涌澎湃的胃痉挛不时袭来,痛断肝肠。后来找一位老中医调养,勉强好起来,但一喝啤酒,便狂泻不止。
来京城快20年了,再没喝过啤酒。偶有老友来京,说起当年一起喝酒的情景,不禁感慨系之。据说济啤后来被青啤兼并,白雪、北冰洋、黑豹已难觅踪影。省府前街那位做酱油螺蛳的“嫂子”,后来死于一场莫名的车祸。当年一起喝酒的朋友如今星散各地,大都到了奔退休的年纪。不知何时能重回大明湖畔趵突泉边,再邀老友,来份花生毛豆,走一扎济南啤酒……
作者白水,20岁来到济南,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十六年沉浸在这座城市之中。离开20年,依然念兹在兹,梦魂尽在泉城的湖山之间。